近年來,“景觀”一詞頻頻出現于與文化遺產保護等相關的文件、論著中,成為熱門詞匯之一;而與此緊密相關的景觀考古學亦處于起步階段。千百年光陰中,先人如何與遺址之外的周邊環境打交道,又在環境中留下了怎樣的足跡?應用景觀考古的方法,考古學家或許能夠繪制出人與自然和諧互動的“連環畫”。為此,記者就景觀考古學的學科特色和應用前景等問題采訪了相關學者。
目標:破譯雕刻在土地上的文獻
古人不只曾在今天所見的遺址中生產、生活,還與周邊環境存在各種互動形式。景觀考古學就以這類遺址周圍的情況作為研究目標。
在西方,“景觀”概念興起于近代,與藝術學、政治學、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多個學科有著密切聯系。它從藝術上的風景畫、園林設計等逐漸進入其他學科領域。19世紀初,德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洪堡將“景觀”引入地理學研究。20世紀,景觀生態學在西方發端并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此后,社會學與人類學等學科也吸收了“景觀”概念。“景觀”這一概念復雜且應用廣泛,在多個領域都有不同的闡釋和應用。
對于景觀與考古的關系,英國考古學家克勞福德曾以一張反復書寫的草紙做類比:“景觀就像一個反復寫作又再三被擦除的文獻,考古學者的工作就是要破譯它。考古學者研究的遺跡包括道路和土地邊界、樹林、農場,以及其他人類居住地,進而包括所有人類勞動的產品,這些就是人類雕刻在土地上的文字。”
景觀考古學同樣是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地理信息系統、遙感等新技術的出現,為信息的采集、處理提供了更為精確的手段。在理論方面,人文地理學、現象學等學科取得了長足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人類學界開始討論環境與人的互動關系。在理論與方法均走向成熟的背景下,景觀考古學誕生并且成為推動文化景觀研究的動力之一。
應用:呈現洋溢人文氣息的歷史“景觀”
與傳統環境考古學相比,新興景觀考古學更加強調人對周圍環境的理解和認識,強調景觀中的人文因素。景觀考古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將人為與自然元素聯系起來,例如山川河流屬于自然景觀,但是人類又在這些景觀中活動,所以人類的行為實際上也參與了景觀的塑造。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張海認為,景觀考古的核心內容有兩方面:一為景觀歷史,也就是人類對其生存環境的土地利用的歷史研究,這是景觀考古的基礎,也是正確理解考古遺存存在及如何存在的基礎;二是景觀構成,是空間文化價值的構建。景觀考古的優勢在于關注連續的地表,將人類的活動與其生存的環境整合起來。
景觀考古學是從文化角度來看自然環境的,這與當下的環境考古注重自然環境變量有所不同,類似于文化地理與自然地理的區別。吉林大學文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陳勝前表示,景觀更強調人與環境的交融,是人的生活與體驗,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風水”即是一個典型的景觀概念。
牛津大學考古系主任切爾斯·戈斯登特別強調,研究人類與自然景觀的互動,現代技術手段如雷達、航空照片等被用于提供大尺度的景觀變化,所獲材料怎樣與地面調查、地面發掘等所獲小尺度的景觀變化材料結合,以及各個學科的研究如何整合,是值得研究與探索的重要問題。
前景:中國或成景觀考古學之沃土
學者表示,中國擁有豐富的考古材料和壯觀、多樣的景觀,可為景觀考古學提供大展身手的空間。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也需要景觀考古學的參與和支持。
景觀考古可以看作是人地關系研究的中觀理論,在環境考古、地質考古與遙感考古的整合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這個領域。張海告訴記者,景觀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應更多關注考古學本身的學科特征,關注對考古資料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古代遺存的生存和發展歷史;第二,多學科交叉產生的新領域系學術的增長點,中國考古學界應著力思考理論的建構問題,而不能僅局限于以西方的理論闡釋自身文明。
景觀考古對中國考古學的啟發、借鑒意義主要集中于人文方面。陳勝前告訴記者,景觀考古是從人文角度來研究環境的,與環境考古從科學角度研究環境是不同的。而缺乏人文正是當代中國考古學需要彌補的弱點之一。
談到中歐景觀考古學的異同,戈斯登說,近來歐洲考古學界也在反思景觀是持續的過程還是變化顯著的過程。此前,一般認為,中歐在景觀認識方面的差異是其地理條件不同的結果,中國具有面積廣大、適合農耕的中央平原,而歐洲則不具備這種地理特點。因此,歐洲的景觀考古更強調變化;而中國擁有持續發展的歷史,所以中國考古學更強調景觀得到持續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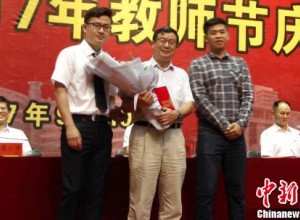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5919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5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