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寧:反思拉·維萊特公園設計
個人簡介:
朱建寧,1962年4月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80-1984年就讀于南京林學院林學系,獲園林專業學士學位,1986-1990年就讀于法國凡爾賽國立高等風景園林學院,獲景觀設計學博士學位,1990-1995年在法國著名的謝梅道夫(A.Chemetoff)景觀設計事務所(BureaudesPaysages)工作,任項目負責人,1995年3月回國工作,現任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規劃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0年成立北京北林地平線景觀規劃設計院,現任國家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國家建設部風景園林專家組專家,《風景園林》學刊編委,西南大學客座教授數職。

朱建寧
主要事跡:
提到歐洲園林,國內很多設計師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凡爾賽宮苑,而是在2000年后被人們熱烈談論的一個稍顯陌生的名字:拉·維萊特公園。因為它不僅是歐洲近現代園林的代表作之一,更憑借所謂“解構主義”的設計思想和另類新奇的建筑設計成為國內一些設計師廣為模仿的樣板。但是,在近一段時期,國內多位著名設計師卻無一例外地對拉·維萊特公園的設計理念、手法和應用元素以及對它盲目模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到底應該如何認識、看待和學習這座頗具爭議的現代名園,記者為此采訪了西方園林史專家、北京林業大學規劃教研室主任朱建寧教授。
記者:拉·維萊特公園的產生背景是什么?
朱建寧:拉·維萊特公園誕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值法國園林復興運動初期。在此以前,園林在社會上的地位非常低,作品也基本上是一些所謂的綠地,強調的是簡單的休閑、衛生、體育、環境等功能,對公眾,特別是中青年人群的吸引力非常小。于是,在園林復興運動中,很多設計師開始思考,怎樣才能將人們重新吸引到園林中去,以及現代化的城市究竟需要怎樣的園林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不論是拉·維萊特公園的業主還是設計師屈米,都意在創造一個與以往園林風格大不相同的作品,一個21世紀公園的樣板。
記者:那么,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拉·維萊特公園設計又有哪些積極意義?
朱建寧:我認為有三點。第一,拉·維萊特公園的一個主要設計思路是,城市公園要做到“園在城中,城在園中”,改變傳統園林和城市截然分開的狀況,創造一種公園和城市完全交融的結構。這種融合并不僅僅停留在諸如由公園林蔭大道向城市立面延伸等簡單的層次上,而是要嘗試如何將城市和公園完全融合在一起,做到城市里面有公園的痕跡,公園里面也有城市的建筑和格局。
第二,設計師在設計拉·維萊特公園時希望做到“白天看公園,晚上看夜景”。在其之前,法國大多數公園只在白天開放。而屈米認為,真正需要公園進行身心放松的工作人口白天根本沒有時間去公園游覽。所以晚上公園也應該開放,而且要有美麗的夜景。同時,他還認為,通過夜景照明,吸引大量市民,可以形成很旺的人氣,使城市公園避免成為各種犯罪的滋生地。也就是說通過公園設計,減少犯罪的幾率,改善社會的行為習慣。
第三,屈米基于城市變化理論提出了可塑性空間的設計思路。他認為,城市時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公園周圍土地的利用形式也難以預料。因此,很多時候,城市的擴展往往使得原先的園林顯得與新環境不再協調,成為了一個老園;而新建的園林也會與舊有的環境不協調,表現成一個新園。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屈米希望建造一種具有可塑性和柔性的園林空間結構,使城市公園不管城市擴大還是縮小,都能夠與之相協調。而這種結構在屈米的設計中主要通過一些網格以及網格節點上的亭子進行控制。這些網格本身具有一定的伸展性,并向城市空間延伸,去控制城市空間。
記者:這樣看來,拉·維萊特公園的設計理念在當時還是比較新穎的,那對它的批評之聲又來自何處?
朱建寧:盡管在當時,拉·維萊特公園的設計理念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在實際設計中,屈米卻試圖用建筑的方式來追求一種與傳統園林截然不同的效果,但這種建筑化的思路不幸走向了極端,結果丟掉了園林崇尚自然的本質屬性,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國內很多設計師熱衷于談論的拉·維萊特公園所謂“解構主義”的設計手法,實際上就是用一種解析的思路,將傳統形式的園林分解成各個元素,再用新的功能把這些元素重新組合起來。設計師屈米沿著這樣的思路,從法國傳統園林中提取出了點、線、面三個體系,并試圖通過對這三個體系進行疊加和組織,來形成一種新的園林結構,這種手法曾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十分流行。
但屈米在完成抽象形式的解構之后,卻運用了大量建筑元素作為具體的表達形式。傳統法國園林中由綠籬、雕塑所形成的“點”變成了一個個紅色的亭子;用林蔭大道、樹墻構成的“線”變成了由建筑形成的廊架;用叢林、花壇、水池等表現的“面”則變成了單一的草地和鋪裝廣場。因此,可以說拉·維萊特公園是一個主要以建筑元素和硬質材料構建的園林。
而現在看來,這種建筑化的園林一開始就有幾個明顯的缺陷:第一,造價非常高,每平方米造價為2000至4000元人民幣,而現在歐洲公園的造價一般也就是200至300元人民幣;第二,盡管很多建筑的造型非常奇特,但過于裝飾化、時裝化,過不了多久就讓人感覺到過時和厭倦;第三,公園的整體氣氛更像是一個游樂場,而不是供人接觸自然的公園。
記者:造價過高、盲目追求古怪新奇等類似的傾向在我國目前的園林建設中也的確存在,拉·維萊特公園在這方面似乎是一個反面教材?
朱建寧:的確,拉·維萊特公園已經成為當代法國風景園林師批評園林建筑化設計語言的實例。而其在法國的影響力也遠沒有它在中國那么大。法國權威機構編寫的《法國園林指南》,從無星級到四星級給該國550多座公園打分,拉·維萊特公園只得到了兩星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建筑化的設計語言卻受到當前國內很多設計師的推崇,并在不少項目中或片面模仿其解構主義設計手法,或追求與其類似的新奇花哨的眼球效應,而忽視了對園林自然屬性的追求。這種對建筑師設計手法的片面理解和盲目模仿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警惕和反思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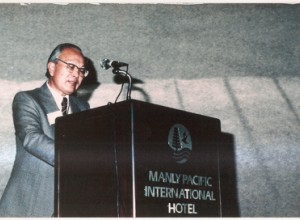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5919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5919

